「大宮教授、上杉先生,不好意思,我回來了。」優奈帶著蒼白的臉色緩緩走進來,就在她看到米砂的同時,原先那股令她作嘔的味道,又再度衝擊她的嗅覺,而且比先前還要強烈許多,令她不得不再次奔離研究中心。
「真是傷腦筋。」真實嘆一口氣,把嘴中的煙斗收回口袋,或許是因為米砂的身高比自己還矮,他不經意將眼前的米砂當成小孩子,輕撫她的頭:「我想我得離開了,我不能不顧慮我的助手,下次─不,等案件結束後,我再來告訴妳我的經驗判斷好了,或者妳也可以問問大宮教授,好嗎?」
米砂的雙色瞳靜靜凝視真實深邃的藍眼珠,她雖然沒有開口答覆,但冷漠已經從她的眼神離開,取而代之的是莫名的信任感,她自己也不曉得,為何眼前的男人會有這樣的魅力,或許是因為對方溫柔的語氣;亦或神秘夢幻的藍眼珠?
真實對米砂笑了笑,然後向大宮道別:「老頭,下次再見。」
「喂,有空再約黑臉喝酒啊。」大宮提醒,真實背對大宮,揮揮手表示知道。
「酒?」米砂看了大宮一眼。
「嗯啊、嗯,沒事……」大宮猛然想起米砂下的禁酒令,默默返回座位。
不過阿部米砂並非想起與大宮教授的約定,而是想調配一種特殊酒,她小碎步跑到實驗桌前,一一打開大宮偷藏的調配酒,迅速將三種量杯中的藍色氣泡液體相互混合後倒在紙杯中,然後帶著紙杯匆匆離去。
瞧著米砂這一連串不可思議的舉止,直叫大宮瞠目結舌。
阿部米砂小跑步咚咚咚地追出門,看見並未走遠的真實與臉色不佳的優奈,她只說一個字:「給」,把杯子交給真實後,又咚咚咚地踩著小步伐回去。
真實望著米砂嬌小的身軀,頓時發覺米砂或許是個很可愛的女孩。
「喝下這個,妳會舒服很多。」真實將杯中的藍色飲料拿給優奈。
「反正再糟,也不過就是再吐一次。」優奈看著清澈的藍色液體表面不斷冒出小氣泡,雖然會令她聯想到奇怪的化學藥劑,不過她還是一口氣灌入嘴裡,一股清涼而不刺激的味道順著喉嚨吞入翻滾的胃中,隨即沖淡隱隱作嘔的不適,慢慢透出清新舒暢的感覺,原先蒼白的臉色瞬間紅潤起來。
真實看一下手錶,發現時間還早,他詢問身邊的助理:「接下來要去找日下政治,妳就先回家休息吧?」
「我可不是弱不禁風的嬌嬌女!」優奈聽真實這麼一說,一股不服輸的鬥志再度被點燃,只是在真實眼裡卻視為賭氣的孩子,但他並不討厭優奈這樣的個性。
「那走吧。」
「那個……上杉先生,有個問題我想問問。」優奈突然神色嚴正詢問。
「問題?」真實雙手插入口袋回答。
「福馬林的味道我能忍受,但大宮教授與那女孩身上有一股強烈的味道,就連福馬林的刺鼻味都被那股味道壓住,那是什麼味道?」
「原來妳是要問這個。」真實神秘的笑了一下:「這個嘛,我還是先不告訴妳,我擔心如果告訴妳那是死人的味道,妳可能就不會想再成為刑警了。」
「死人……的味道?」優奈停下腳步,一雙大眼居高臨下盯著眼前比自己矮小很多的男人。
「……」真實也停下腳步,不知道要說什麼。
「……」
最後,真實被那雙大眼瞧得混身不自在,只得這麼解釋:「我應該沒說那是死人的味道吧?」
「你說了,我聽的很清楚。」優奈雙手插腰嘟著嘴微微彎下,臉頰微微透露出才剛恢復的紅潤血色,令她看起來可愛極了。
「可以當作沒聽到嗎?」不過真實卻不敢看向她,急忙掏出煙斗叼在嘴上。
「當然不行,我還得怪你為何不早點說,這樣我會有心理準備。」真實聽優奈這麼回答,忍不住會心一笑,這女孩真的很有趣。
兩人在下午四點前趕到日下政治位於櫻丘町的居所,同時也是火災與日下三四的命案現場。
近傍晚時刻,金色的陽光被染紅,橘紅色的黃昏如同四季的冬末般殘存。
數十坪大的灰色房屋,被橘光映照,更顯蕭條寂寥。
警戒線將房屋圈起來,看守的員警沒昨天多,只有在前後門各留兩名警察看守。
真實直接表明與日下議員有約,警察並未刻意刁難直接放行。
兩人並未進屋,而是直接從前庭繞到後庭院。
日下政治一個人站在修剪整齊的草地,黃昏的光芒曬在他的略嫌窄小的肩背,灰黑的影子拉得老長,一人一影更突顯出他的落寞。
「初次見面,日下先生。」真實將夜巡者事務所的名片遞上,日下政治的臉色顯得有些疑惑。
「你不是電話中與我約好的東京產險……」
「不,我只是接受東京產險的委託。」
「什麼?」日下政治忍不住大笑,只是這笑容隱藏著無奈:「我對於賠償並沒有什麼特別要求,不需要另外再委託……嗯,徵信社來……你們算是來調查的嗎?我不太能理解東京產險想要做什麼。」
「我想你可能因為令尊的死,情緒無法平撫下來,思緒也還未理清,希望你能先冷靜下來,仔細去思考一些細微的事,甚至是瑣碎的無關緊要雜事也可以。
我會代表東京產險來到這裡的理由,你不可能不知道,日下三四雖然已經脫離權力核心十多年,但不代表他不知道某些秘密,這可能涉及黨團或是兩黨之間的問題,夾在中間的東京產險可是非常為難,若一不小心處理不好,就算東京產險身為首屈一指的集團企業,面對黨派這樣的權力巨獸同樣得乖乖屈服,更何況這還關係著兩隻鬥爭的權力惡獸。」
日下政治聽完真實的解釋,默不作聲走到盆栽前,蹲下來輕輕撥著被微風吹動搖晃的黃色向日葵。
「你想知道什麼,問吧,但我希望我們之間所談的內容,只有在場的兩……」日下政治的口氣停頓下來。
「既然你信任我,也得相信我信任的人。」
「信任?」日下政治嗤之以鼻:「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可以信任!」
「如果有你不能透露的事卻說與另一人,就代表你打從心底相信對方,不論你承不承認,那怕你只是把對方視為一張救命王牌來利用。」
「隨你怎麼說,總之若真的從我口中掏出些什麼秘密,到時只會多增添一具屍體罷了。」
「那種事絕對不會發生。」
「哦,你那麼有把握能在權力惡獸的血口下保護我?」
「當然不能。」
優奈與日下政治聽到出人意表的回答,兩人十分驚訝,這種情況之下,不是都該回答:「當然有把握」嗎?
「我不敢保證你一定沒事,因為我只會保護我自己的人。」
優奈聽真實這樣的回答楞了一下,隨即恢復正常,她猜想真實應該是受父親所託,所以才能不經思索講出這番話來。
「原來如此……」反倒是日下政治蹲在地下喃喃自語,不知在想些什麼。
「當然,如果你願意委託我的話,我也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委託?」日下政治猛地起身,炯炯有神的眼光射向真實,他這時才發現對方有著一對神奇的藍瞳,帶著絢麗多變的異樣光采。
「從你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來你擁有很多想要保護的人,而你也是一個極需要受保護的人。」真實從日下政治的眼中看到了無助:「不過委託的事,還是先等這次的事件解決後再來談吧。」
「那……你想問些什麼?我已經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訴立花,你們應該聽得很清楚。」日下政治從桶子中拿出灑水壺,替盆栽中的向日葵淋上水。
「這個嘛……對了,你現在頭還痛嗎?」
「頭痛?」日下政治遲疑數秒,才恍然大悟:「不痛了,吃過藥就不疼了。」
「昨天也是?」
「昨天?哦,是啊。」
「藥效那麼強,可以借我看一下是什麼牌子嗎?」
「嗯。」日下政治從口袋拿出頭痛藥給真實,真實點點頭默唸數次品牌名後,才還給對方。
「那麼我想請問一件事,你還記得最近一次令尊曾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的事嗎?」
「沒記錯的話是前年,那場車禍的前一天。」
「他是否曾說過奇怪的話?」
「奇怪的話?沒有,雖說他醉得一塌糊塗,但仍能自己走回來,反倒是隔天酒未醒卻出車禍,這件事令我感到相當意外。」
「昨天我從附近鄰居打聽到,令尊在出車禍那天的舉止有些怪異。」
「怪異?」
「據說當時並沒有下雪,他卻嚷嚷著什麼雪,他是否有眼疾,或是喜歡白雪?還是有什麼與下雪有關的畫、詩、詞、俳句或藝品之類的東西?」
「不,等等,你這麼一提我才記起來,喝醉酒的那一夜,他的確講過雪之類的話,當時我並沒有很在意,以為只是冬雪月那類名酒,至於家中有沒有與雪有關的東西,我印象中沒有。」
真實拿起沒有點燃的煙斗放入嘴中:「那麼這個話題先丟在一邊……倒是有件事我很好奇,有關於你所創立的人本基金會。」
「基金會?」日下政治不明白對方怎麼會問起無關緊要的事。
「是的,人本基金會主要運作是提供海外地區的日僑、日裔孤兒認養事宜。」
「這有什麼疑問嗎?」
「在這一百多人的名單中,我對一個叫日下五月的少女很好奇。」
「日下五月?」日下政治嚥下口水才回答:「應該是住在加拿大十六歲大的孩子?」
「嗯哼。」真實點點頭繼續說:「那麼前田大輔?」
日下政治摘下多餘的枝條,停頓數分鐘才回答:「可能是住在台灣的……一個小男孩。」
「住在墨西哥的知本小夜?」
「我對知本小夜有印象,但是不是住在墨西哥就不太記得。」
「在這百餘人中,所有人的補助只有到大學或十八歲就業,但是……」真實沒有繼續說下去。
「你的疑問,應該是來自於那名叫日下五月的女孩為何能獲得終生補助的事吧?」
「的確是,不過這個問題單純只是想要滿足我個人的好奇心罷了。」
「好奇心?如果我說那是我們日下家族移居海外的遠親呢?」
「為何不直接說是你認養的孩子?」
「因為我沒有認養。」
「令尊認識她或她的家人?」
「……我現在可以改口說她是我想認養的孩子嗎?」日下政治停止拔除分枝的動作,再次拿起灑水壺澆向旁邊的盆栽。
「可以,不過令尊認識嗎?」
「不認識,完全不認識。」日下政治不懂對方為何一直追問這件事。
「你確定?」
「我父親的確不認識那孩子,但……」日下政治或許不想在這個問題打轉,直接了當告訴真實:「我父親與那孩子的父親有些關係,僅僅如此,這件事我只能說到這裡。」
「這樣看來,你或許比令尊對這件事了解的程度更少。」
「什麼意思?」
「你知道你父親為某人創立秘密基金會的事嗎?」
「什麼?」日下政治回頭看向真實,他的眉頭皺成一團。
「那個人就是日下五月。」
咚地一聲,灑水筒落地,所剩無幾的水濺濕日下政治的褲管,當事人卻毫無知覺,如傻了般站著。
日下政治的神情從一開始的皺眉瞬間轉換成呆滯的模樣,就可知道這件事令他感受到相當大的震撼。
真實替對方撿起灑水筒,幾乎被修剪齊平的綠草,沾上大量水珠,草皮上也積了一小灘水,他伸出右手撩撥一大片沾著水珠的草葉,隨後將灑水筒放入水桶,裡面置放的東西與昨天一樣。
「日下先生。」真實用掌心習慣性推了推藍色鏡框,打斷正處於驚嚇狀態的日下政治:「日下先生。」
「是,不好意思……」日下政治總算回過神,他轉過身去,欲再一次摘下多餘的枝條,只是這次卻不小心摘下一朵鮮豔奪目的紫色玲蘭花,垂下的鈴狀花朵散發濃郁的花香。
「對了,這裡的草皮修剪的很整齊,是請工人來弄的嗎?」
「不,這裡是家……亡父的後花園,容不得任何人染指。」
「七十歲的年紀親自割草?」
「割草?」日下政治無法理解真實問問題的重點所在,他對東京產險委託偵探來調查的事感到不能理解,更何況眼前這名偵探還是一個很古怪的人,所提出的疑問與回答完全跳脫正常人的思維,他想了一下,最後還是回答真實的問題:「是啊,連親生兒手都無法染指,更何況是別人,這裡的一切,亡父絕不假手於他人。」日下政治講完話,抬起手準備把手上的紫色小花丟掉,但不知為何卻停在半空中,最終還是沒丟棄。
真實叼著煙斗,眼神變得銳利起來:「他沒用過除草劑?」
「除草劑?不,亡父就連種花都沒用肥料了,更不可能會用除草劑。」日下政治十分肯定。
真實聽完日下政治的回覆,他將煙斗收回口袋,眼光望向一旁的水桶:「看來真正的嫌疑人找到了!」
圖/文/きまぐ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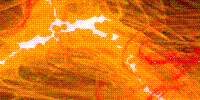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