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項刀聽聞父親最後一役的戰事已經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當時項羽與劉邦立下鴻溝和約後,遭到劉邦毀約背信,卻反被項羽在固陵痛擊,並將其困守於廣武。
項刀得知戰況後,隨即動身欲往前線,未料大司馬周殷叛變發動屠城行動。
項刀為了安民,招集部份兵馬自南往北,一路平定周殷所犯下的暴行,但已無多餘的兵馬能夠守城,最終不得不放棄九江領土,急奔固陵前去,並派人先行告知項羽九江局勢,豈知終是慢了一步。
周殷與英布會兵於垓下城外,前路遭到大批兵馬封鎖,項羽被困垓下。
項刀見狀,明瞭憑自己的能力與少許的兵力是無法為父親解圍,再加上自己深知以父親的武勇定能突圍,而渡烏江是唯一可以脫困的路線,所以他決定先渡江返楚地,穩定江東人民的信心,再遺兵馬去烏江接應父親。
焉知江東已亂,留守江東的項伯、季布等人以安內為由,發佈戒令不肯出兵,鄭君、共尉等人與其對立,欲集大兵援救受困垓下的項羽。
項刀與一眾鐵騎還未入城,便先派人打探而得知此消息。
「項伯這賊人!不得好死!」一眾死士與項刀在城外一處歇腳的茶店,聽完來人回報,眾死士紛紛大怒。
其實楚國陣營並非團結一心克敵,其主因在於項伯私下與劉邦交好,且三番兩次與項羽唱反調,只求安定楚地力保不失,又意欲與漢合盟。
這次簽下鴻溝和約,也是項伯力排眾議極力要求下,項羽迫不得已才決定,豈知竟是無法回頭的路,難道這其中沒有什麼貓膩?莫不是項伯同劉邦伏下這死局?
若非項羽重情份尊長者,身為項羽叔父又如此昏庸的項伯,焉有如此大的權力?
故項羽身邊忠誠的死士,向來都對力主談和一派的項伯非常憎惡。
「我們辛苦打天下犧牲生命,不是為了這隻只會對著無賴乞求的項狗!」
「若不是那項狗,劉邦早在咸陽關中宴被項莊宰了!」
「沒錯,項兄弟,不能讓霸王辛苦奮戰建立起來的楚國被這隻狗賣了,一定要殺了他!」
眾死士鬧哄哄的準備集結起來,驚得那茶老闆不知躲到何處。
反倒是項刀一語不發面容肅穆,他雖然年幼個性又豪邁,但曾受過范增的提點,知道愈是處於危機之際,愈不能自亂陣腳,必須要以更沉穩的心態去觀察戰局,所以他一直沒有對眾將士的意見有何反應,眾人喧嚷好一會,才有人注意項刀並未加入談論。
「項兄弟?」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不過現今戰況嚴峻─」
「報!」項刀還未說完,便有一人駕著馬十萬火急奔至,只見這人一臉哀愁眼眶泛紅道:「霸王自刎了!」
「什麼!」眾將士楞了一會:「他奶奶的,二楞子你新來的啊?這種消息不盡不實,你打那聽來的?」
「渡江而來的漢軍。」
「渡江!」眾人聽完二楞子的答話,又是一驚:「漢軍已然渡江!」眾人頓時心頭大亂,紛紛看向項刀。
「你先冷靜下來,將此事細細說來。」項刀皺眉問道。
這二楞子先緩了口氣,才娓娓道來……
原來二楞子先行至江邊打探消息時,漢軍已渡江設營,二楞子身著百姓服裝很難混進漢營,因而找了個落單的士兵宰了,換上服裝潛入營地。
因為不知道漢營口令,所以二楞子也不敢混入營陣中心,只能隨便找個外圍營地逛逛,有十多個小兵升了火正在用餐。
「是真是假?」
「真啊,比我這真金十足的金牙還真!老弟我的老哥可是在絳侯底下做事的,怎可能假!」這小兵刻意露出嘴中金牙,以表示所言確實。
「沒想到這項羽……竟然想不開,自刎了。」
「就是,明明已經渡江可以返回楚地,卻不知又發生什麼事,自殺了。」
「不知項羽所用的那把黑刀和戰戟被誰瓜分去了?」
「戰戟好像讓楚兵帶走了,至於黑刀嘛,當然在漢王手中!」
「不知那神兵利器會賞賜給誰?」
「嘿,這刀誰都沒資格用,漢王說很敬重這霸王,打算為他建個兵塚,這刀可不能賜!」
「可惜啊!」
「哈,再可惜,也輪不到你!」
餘下眾人吃吃喝喝胡鬧一番,再講下去也只是戰事歇了,要回去見自家婆娘等等風流之事,二楞子沒再聽到更多確切的消息,於是又去其它營區探聽,所聽聞的消息皆盡如此,因而趕緊回來稟報。
項刀聽畢,頓時臉色蒼白,好半晌才緩緩道:「去狡窩!」
「不回城嗎?」眾兵疑惑。
項刀上馬眺望向西方,也就是眾人傳聞項羽在烏江自刎的方向,徐緩的風自西迎面拂來,似是與他同哀。
這時節已是冬臨,枯黃的落葉伴隨著沒有目的地的微風在空中飄渺無蹤,眾人上馬看著項刀的背影,似是感受到蒼茫蕭瑟的哀痛,項刀竟泫然欲泣而不自知,回答適才那人的問題:「待父王死訊傳至項伯等人耳裡,恐怕是各立為王,這江東危矣。」
「項兄弟,我們可以舉你為王!」
項刀搖頭:「上不只有范姓兄弟姐妹,我又為庶且名不正,怕是無人擁戴,而以劉邦之盛,又有張良、蕭何、韓信等人相助,不過幾年天下將平,又何必累得江東父老再受戰火煎熬,收手吧,大江……東去不復返……」項刀話中語意未盡,卻嘔了一口血墮落馬下。
「項兄弟!」
……
「項哥哥!」
項刀半昏半醒之際,似乎聽到有人在喚他……
「別再項哥哥長項哥哥短的,肉麻死了!」聲音略顯蒼老嘶啞的人嘮叨著,聽來該是位老人家。
「咱不要您管!咱就喜歡這麼叫!」嗲聲嗲氣的妙人兒卻這麼回那老人。
「小妮子都多大了,還在項哥哥、咱的咱的,不是和妳說別用咱這字。」
「誰叫爺兒打小就這麼教咱的!」
「妳、妳─咳─咳,也不可憐可憐我病體微恙,就這麼咳、咳和我頂嘴啊!」老人猛地咳了一陣。
女子雖然和老人拌嘴鬧著,但一發現老人舊病復發後,手腳卻很俐落地從瓶中倒出藥丸,和著酒水讓老人喝下,老人的咳聲才漸漸停歇。
「爺兒再撐著點唄,再服四劑就可康復啦!」
「老了,不中用啦!」老人突地冒出這麼一句感慨的話。
「怎地說這種話。」女子親暱地勾著老人瘦小的胳膊,向他撒嬌道。
「妳啊,還是早點和那小子成親,快點弄條人命來給我逗逗!」老人卻向女子調笑。
女子卻呶呶嘴,繽粉的小臉蛋旁酒渦、梨渦齊放:「小子小子叫著,說起這還不能怪您嚒?」
「怪我?」老人奇道。
「按年紀來看,您可是人家的爺兒;若按輩份,爺兒該是人家的叔伯,可身為孫女的咱又是被婚配,結果爺又和人家稱兄道弟,這輩份亂來亂去,豈不是亂人倫?」
「這、這事一碼歸一碼。」老人被女子詰責,有些不知該怎麼回答,最後才道:「交情各交各的,我交我的,妳交妳的,這不就好了!」
女子噘嘴不依,老人哈哈大笑。
「不好啦!」門外忽地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自遠而近,只聽這女孩聲音稚氣未泯,柔順的清音叫人聽來舒服,待得這女孩推開門道:「又死……」
項刀稀稀疏疏聽到這幾人談話,片刻又昏了過去……
……
「項兄弟醒啦!」照顧項刀的人高聲一呼,大伙人湊了過來,項刀見這些人鬍子皆未打理,與鬢髮連成一線,那裡像是個兵,這會兒瞧來個個倒像是匪徒。
「我昏了多久,這又是那?」項刀腦袋仍有些昏眩,他勉強坐起身來。
「不過五天,打從周殷這土匪投了漢王,你便沒好好休息,又聽聞霸王……總之,你累倒了,我們現在身處狡窩。」這人急忙取了水袋給項刀。
項刀飲了一口水後覺得好很多,腦袋也清醒了些,總算想起昏迷前的事,聽聞父親自刎後,他打算領眾人來狡窩,殊不知卻暈了。
項刀環視眾人見著一個個熟悉的面孔,回憶起這三年與諸位所經歷的各種大大小小的戰役,不只擁有共生死的情誼,更有亦師亦友的情份,如今……
「現在不算我,這剩多少人?狡窩藏的財寶有多少?」
「三十三人,狡窩財庫約有一百六十六萬兩。」
「每人分五萬,然後將這封了,大家各奔東西。」
「什麼?」眾人大驚。
「項兄弟視我等為貪婪之輩?」
「吾等有傲天之志,不求錢財,只為追隨霸王平定天下!」
「我胸無大志,只是平生敬佩霸王的英姿與武勇而追隨,不是為了賺取白花花的銀子而活!」
「……」
項刀這番話對大多數的人極具誘惑,但對這群死士卻非如此,反倒引起一陣騷動,眾死士紛紛表明立場。
項刀揮揮手要大家冷靜,待大家不再出聲,他才解釋道:「我從未認為諸位滿腔熱血的兄弟們,是視財如命之徒。
只是這筆錢財本來就是父王預備要留給你們安家用的,你們也知道自己是編制外的部隊,所以父王會將一部份的錢財分撥二處狡窩,知道的人很少,但都是父王信任的人,這處狡窩就是為你們而設,另一處狡窩是父王身邊的那支部隊。」
「縱使如此,戰事未平,天下未定,項兄弟豈可將此財寶先分送給大家?難道……」
項刀點頭肯定對方的猜測:「父王已然離世,這天下已是劉邦的,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眾人聽畢,許多人低頭不語,更有人不復先前堅強,忍不住在大家面前落淚。
「蒙諸位不因我是霸王之子而另眼看待,待我又如師亦友,項刀與各位是過命兄弟,這不是永誌難忘的事,而是用血刻印在身體、心頭的事實……
我相信,父王若復生,此時此刻也會與我做相同的決定,父王心中憾事定與我現下心中所想一樣。」項刀說到此處,炯炯有神的雙眼不禁流下英雄淚:「世事本無常,有聚必有散,分離是不可避免,別人飲血酒方為兄弟情,但我們不須如此,因為我們已經用熱血互相見證仍活著的彼此。」項刀高舉握拳的右手同眾人立誓。
在場的眾人,無一不是用自己的鮮血護住身旁的弟兄,戰爭所受的傷痕不是只刻印在身上,留下無法抹煞的痕跡,更是遺留在心頭中,永難忘懷的悲愴;身邊兄弟飛濺的鮮血,不是只染在身上的紅衣袍,而是連生命刻痕也印在染紅的戰甲上。
這種同袍間在戰場上經歷的過命之交,遠非那江湖上風花雪月之事可以比擬。
餘下三十三人同項刀舉起右拳立誓,他們在臉上流下的不只是英雄淚,更在心中留下無法抹滅的遺憾。
最終,三十餘眾各奔前程。
項刀浪跡天漄。
十多年後,項刀偶遇丰老,機緣湊巧之下取回父親的黑刃直刀─霸王刀。
之後的某年,因為某事件的爆發,遇到當年待在父親身邊的死士,終於得知父親猶如傳奇般的最後一場異事,爾後更是遠赴西域手刃仇敵。
而這又是項刀另一段在西域傳說的故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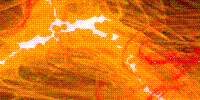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