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壽殿,外觀宏偉內殿裝飾更是華麗極致,然而深閨之中,卻是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白紗與紅木傢俱,這是太皇太后呂雉的閨房。
「娥女去告訴右丞相,我死了以後將食其改任……太傅。」
「是。」娥女輕啟寢門去尋陳平。
「唉。」呂雉喟然嘆息,不知為何潸然淚下,兩行清淚滑落至未見歲月痕跡的白皙臉龐,她望著銅鏡裡的自己已年過六十,鬢髮未白、容顏未衰,心思卻有如七、八十歲老婦般疲憊不堪,縱使審食其能解心中一時苦悶,卻無法真正了解她。
無怪乎呂雉有此想法,北宋六一居士歐陽修曾著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治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
此詞寫的是暮春閨怨,呂雉雖位居漢朝權力中心高位,卻是孤身獨處,心事哀怨無以為訴。
倏地,燭火微微一晃,鏡中多出了個人影,呂雉本以為是娥女回來了,怎料鏡中的身影愈來愈清晰,此人面容模糊卻看得清楚白髮白鬍,身著皇袍負手悠然緩步接近,呂雉手中的白玉梳落於桌面,叮噹聲響環繞於耳際之間,不絕於深閨內心,呂雉身還未轉,臉頰未乾的淚痕又滑下兩行晶瑩水露。
「是您未死,還是娥姁身陷地府而未知?」呂雉玉手捧心,臉色既似滿心期待又似驚慌。
「悠遊於夢,似真還假,夢若是真便是真,妳若認為是假便是假。」一聲蒼涼威嚴的口氣自鏡中人影口中說出。
「不論似真若夢,娥姁總算又見到您了。」呂雉轉身望去,見著了這日思夜夢的人,正活生生的站在自己眼前,十五載已過,白髮蒼蒼鬍鬢已白,面容滿是歲月的刻痕,卻無損於此人威儀,然而嘴角微微上揚的笑容卻帶些許痞子氣息,這人正是那無賴皇帝─劉邦。
呂雉未等劉邦開口,就已撲在他的懷裡毫無顧忌的嚎啕大哭,劉邦憐惜般伸出那粗糙的老手輕撫她柔順如雲的秀髮:「再哭下去,那些宦者會闖進來的。」
「太后、太后,請問─」劉邦話才說畢,門外宦者果然出聲詢問。
「沒事,待娥女回來先在門外通報,等我吩咐再進來。」宦者應聲後,呂雉鳴鳴咽咽好一會才停止。
呂雉待心情平靜下來,抬起頭來含情脈脈望著劉邦。
劉邦見她雙瞳翦水依人、風情萬種,令劉邦想起年輕時的風采,輕輕吻向她嬌艷欲滴的嫰唇:「美人滿懷抱,江山棄深淵,仙天賜予的瓊漿玉液那及得上娥姁的玉津香甜可口。」
呂雉聽劉邦這麼一講,嬌羞得又低下頭去,劉邦見著呂雉那白嫰的玉頸更加不欲罷手,將她緊緊攬在懷裡。
「您怨娥姁、恨娥姁入骨嗎?」兩人相擁片刻,呂雉鶯聲婉轉問道。
「遠朝廷而忘其事,又有何怨恨。」劉邦語氣聽來並未帶任何的情緒。
「您地下有靈,總該知曉娥姁做了那些事?」
「我只要知道,妳替朕將這大漢王國治理的很好,這已足夠。」
呂雉聽畢又低下嬌顏,玉頸微微抽動。
「怎又哭啦?」劉邦輕撫呂雉那依舊柔嫰光滑的美背安慰道。
「您不怨娥姁、恨娥姁,但娥姁卻怨您、恨您為何如此早走,獨留我一人。」呂雉嗚咽道。
「唉。」劉邦深深嘆氣不再出聲。
「您氣娥姁了?」呂雉句句細語輕聲,劉邦依舊不講話。
「朕該走了。」二人沉默一柱香餘,劉邦輕輕放開呂雉。
「這次您又要捨娥姁而去了嚒?」呂雉卻不放手,緊緊擁著對方。
「情緣已盡,妳我不同道,這次怕是妳棄我而去啦。」劉邦輕掰嬌妻玉指,留下這麼一句話後,身影有如迷霧般消失。
「季、季,別離開娥姁,別再次離開我……」呂雉跪倒在地,口中苦苦喚求劉邦別走。
「太后、太后,娥女進來看看您啦。」娥女在門外稟報許久,依稀聽到呂雉的聲音,以為呂雉在見何人,待得片刻卻不再聽見任何聲音,急忙領著門外的宦者進入寢室。
只見呂雉面帶笑容,安安靜靜躺在床上,她甜膩的笑容仿若回到數十年前,與劉邦相處的時光。
「太后、太后……」娥女見狀知曉太后已然離去,她跪在床邊,兩顆斗大的淚珠隨即滴落。
時年呂雉八年孟秋,呂雉病崩,諸呂之亂二月餘,季秋兵變終告結束。
春祭隔日未過午時,丰老著短衣襦褲在醉仙樓瞎混,他在二樓找了觀景不錯的窗邊角落,一個人叫了四罈白乾,桌上擺滿佳餚;香炒鴨肉、清蒸黃魚、醬爆油蝦、辣滷雞腿和一盤豚肉叉燒。
跑堂的上菜時,偷偷向丰老說這盤豚肉叉燒可是得來不易,還有兩日後的羊肉也備好了,丰老笑著吩咐等會再上個玉竹清湯,塞了幾個銅板在跑堂的手中,跑堂的才滿心歡喜下樓。
「明知我不甚愛吃這等油膩菜餚,怎淨叫這些來?」人還未到,聲音卻從遠方悠悠傳來。
「大難已離,又交新友,焉有不慶祝之理。」丰老哈哈一笑,對著不知何時入座的人說道,這人身形偏高,面色有些白,一臉肅穆。
「諸呂已平,又有何難。」這人邊說邊挾起叉燒嚐嚐,配了一口酒,微微點頭表示滿意。
「秦震啊,我們相識多少年?」丰老用手拿起雞腿啃了起來。
「怕也有二十餘年,甚或更久。」此人正是以太尉周勃之名同時聯繫朝廷與江湖共同協力平諸呂之亂的常侍秦震。
「更久?」丰老不解其意,用那隻剛吃完雞腿的油膩的手,在下巴下摸了一會,才將酒倒滿,喝了一大口道:「你可知道我曾在鬼門關前走一遭啊!」
秦震這時才放下竹箸(筷子),表情嚴正望向丰老,丰老就將季秋兵變後續事件做了個交待,還有老王與養蠱人的事,秦震拉開丰老的傷疤一瞧冷笑道:「早點找我不就沒事了。」
「你會解蠱毒?」丰老表情有些訝異。
「略懂。」聽對方語氣不溫不熱,看來應該是真的,丰老嘖嘖稱奇,用著彷彿第一次見到秦震的眼神一樣審視對方:「呂亂剛平,宮中還有許多事要靠你處理,所以我沒去找你。」
「是嗎?」秦震似笑非笑瞧著眼前的老人。
「上湯啦,丰老、爺,打擾!」就在這時,跑堂的送上一鍋玉竹清湯。
秦震頓時眼睛一亮,不顧湯水還冒著陣陣熱煙立即勺上一碗來喝:「這醉仙樓倒是私藏了好貨。」丰老呵呵一笑。
「話說回來,你可知道最近宮裡鬧了鬼?」
「鬧鬼之說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是不是韓信……又在那口大鐘怒號,亦或深幽長樂未央又添新鬼?」
「這倒不是,只是呂雉……呂后死前,似乎見到劉邦的鬼魂。」
「原來是這事,現在才流傳開來,也太慢了。」丰老搖搖頭苦笑,大乾一碗:「宮中大事己定,劉恒在做什麼?」
「倒也勤奮,除了上朝批奏外,偶爾也會玩玩蹴鞠。」
「嗯……」
「別談這些小事,我問你,那黑衣人的身份著墨不出來?」
「我實在想不透那人是誰,但定是那晚偷聽你和呂雉談話的人,也是那近千眾江湖人的其中一人。」丰老十分肯定。
「還有一點就是他是否為苗疆人士,但巴蜀一帶似無輕功極高的人。」兩人談到此處似乎走進死胡同,若沒有更多的線索是無法追查出事情真相。
「姑且不論此事,你瞧王老弟如何?可否……」丰老收起平日嬉皮笑臉的模樣,慎重問秦震。
「還王老弟,不就是邪王卜邪嗎?」秦震啼笑皆非。
「叫著叫著就習慣了。」丰老亦是哈哈一笑。
「卜邪不啻是一代雄才更是一方霸主,能統合巴蜀的確有一手,他有那資格,更有那機緣,但不是現在。」秦震想了一會兒才道。
「除他之外,我還想找之前曾提過的那人。」
「你對他的提攜倒是不餘遺力,若不是早知曉他的身份,我倒以為他真是你流落在外的子孫。」
「我現在就只有那麼一個小妮子,沒別的了。」丰老輕嗤一聲表達自己的不滿。
「最近都在忙大事冷落了她,那妮子可有不悅?」
「嘿,她最近─」
「號外!號外!死人啦!」丰老話語未盡,就有人在街上胡亂大喊。
「江湖那有一天不死人。」秦震斜眼瞄向在街頭奔走的人。
「無上劍的上官孚門主死啦!」
「死了?」丰老與秦震二人對眼相看。
「莫不是你……」丰老別有含意的看了秦震一眼,秦震搖頭:「先去瞧瞧。」
丰、秦兩人結了帳,便往上官府前去,豈料上官府門前集滿了許許多多江湖好漢,大多是前晚在上官府慶春祭的人。
丰、秦二人還未走至門前,便看到兩位當差的亭長離開,其中一人道:「上官這廝可是死的糊里糊塗,毫無外傷又不讓人剖了來看。」
另一人道:「江湖事給他們江湖人了,我們朝廷可還有要事要幹,甭理這事。」
「瞧你說的正經八百,你倒說說有什麼事要幹。」
「還不就找個秀色可人的女子摸摸那白嫰小手,親親那芳香小嘴,就這麼一路摸啊摸的摸上了床。」
「原來你還掛記那賣藝的……」二人漸漸離去,話也愈來愈小聲。
「丰老、是丰老來了!」眾人發現丰老,紛紛讓出一條路。
「這怎麼回事,怎在府前亂成一團?」丰老感到疑惑,詢問周遭的友人,大家七嘴八舌胡講一通,丰老聽了好半會才聽懂。
原來是上官孚暴斃在床上,看似是前一晚飲酒過量導致,因為既無外傷,也沒人進入寢房,房內也無打鬥痕跡。
這事若發生在七、八十歲的老翁身上倒是很正常,可現在發生在一個正值壯年的武人身上,平日亦無病無痛不服藥,這事不挺古怪的?
倒是有些迷信鬼神的江湖人提了另一個說辭,上官孚若不是被呂祿、呂產化為怨鬼暗夜索命,就怕是那巴蜀邪王……
現在眾人擠在上官府前想進一探究竟,豈料上官府擋了人,非上官親屬一律不予進來,除了二位官差來查案和少數幾位與門主較為親近的人才被准許入府,丰老聽畢來由,大罵眾人亂猜測。
「胡言亂語,邪王與上官門主未曾謀面─」丰老話還未說完,身後的秦震卻輕咳一聲,方才轉移話題:「二人更是毫無嫌隙,又怎會用誅心掌痛下殺手。再者,門主武功出奇的高,那怕邪王再厲害,也不可能在不驚動任何人的狀況下殺了門主,別在那亂嚼舌根,待我問明清楚再來答覆諸位。」
丰老請看門的奴僕回去問問主人可否入府,沒過多久,奴僕請丰老入內,秦震跟在後頭也進去了。
丰老與秦震先向家屬示禮,後步入擺放靈柩的廳堂,見有一人著素袍背對廳門,這人聽到丰、秦二人腳步聲隨即轉身,只見此人生得劍眉星目、器宇軒昂,不過雙眼略顯紅腫,看來似是哭過,秦震觀此人嘴角微抿,可以看出這人有些傲氣,但眼白多於黑、鼻朝天,這人恐怕只是個虛有其表的人。
「少門主節哀。」丰老與身後的秦震先向靈柩躬身一拜,才向眼前的少門主拱手作揖。
「丰老,這位是……」
「這位是無上劍少門主上官雲,這位是老兒的朋友秦震。」上官雲見丰老並未多介紹此人來歷,想來並非名士又或另有它意,因此也不多問,等丰老主動開口。
「少門主莫嫌老兒囉嗦,只是想問一問門主如何過世?」
上官雲點點頭,再次說明經過,丰老問及上官孚近日是否與人有嫌隙或紛爭,上官雲作為晚輩當然無不一一詳答,直到丰老詢問是否可以剖腹查明死因,上官雲這時臉色才顯不平之氣。
「豈可如此!」
「難道少門主不想知道,門主是否死於誅心掌?」上官雲聽丰老這麼一說才略顯遲疑。
「少門主,某能理解子孫不願先人遺體再遭受辱,只是門主若遭人殺害而未報仇血恨,怕令先人齒寒、他人不恥,某略懂岐黃之理,不若讓某來診察,並不需將門主剖腹,此議可否。」進入上官府後一直未開口的秦震,卻在此時請求查驗遺體。
上官雲嘆了口氣,思索好半晌才點頭同意:「請。」
上官雲領著二人向靈柩走去,上官雲伸手欲將白布翻看,卻停了好一會,深深吸口氣才將布條拉開。
丰老與秦震見上官孚屍首蒼白、雙眼緊閉,看來死了好一陣子。
秦震道聲失禮,伸出雙指撐開上官孚的雙眼一看,其目已濁而有黑斑,又從懷中取出木片,輕輕打開嘴巴,木片放入嘴中查看,最後伸出右手食、中指輕壓屍身各處。
人既死亡,血氣就會停止循環,屍體自然就僵硬,但逾十二時辰會回軟,紫色與淺綠色屍斑片狀分佈在屍體各處,以指輕壓屍斑卻無變化。
秦震又在胸口與兩側腋窩多做撫壓,片刻後將白布覆回屍首,臉色凝重:「門主屍首完整,經絡脈絡不似有斷結,心室窩未有任何內凹,骨骼完整,門主若不是不勝酒力而亡,怕還真有鬼神之說。」
「當真?」上官雲與丰老異口同聲問道,秦震十分肯定。
「既是天命所為,還請少門主節哀,無上劍還需有人主持。」丰老安慰上官雲後,隨往府外向眾人解釋,命大家先行離開待公祭後再來,最後協同秦震離去。
「有蹊蹺?」丰老和秦震離開上官府後,一路直奔聽雨樓,叫了兩壺清茶
「大有問題。」秦震搖頭:「正值春分,屍首的狀況不該如此,上官孚死亡的時間不對勁,酒宴席散約寅時初,倘使當時就遇害,直至適才驗屍約莫五個時辰,眼濁不該有斑,以指腹壓屍體,紫斑應要退散卻無散,屍首該僵化至極卻已回軟,更不該有綠斑才對,這該是已逾十二時辰才有的症狀,且……」
「且?」
「誅心掌為剖心斷脈,血是不會再集中於心脈,但上官孚死候多時,血卻積於心脈似有未竭。」
「可他明明脈象已無,莫不是要起屍變了吧?。」
「不,或許你們當晚所見之人根本不是上官孚,他早已身亡,而那偽裝成上官孚的人極有可能就是人犯。」
「這人不知與黑衣人是否有什麼關係?又為何殺了上官孚?」丰老想了半天,實在無法理解這其中的關聯。
「那黑衣人該是與上官孚相識,說不定是為了獨吞那樣東西,而將上官孚殺了。」秦震如此推測。
「那現在……」
「你盡快將那兩人約來,我會在二日後子時前找你,宮中有些事我得先處理,還有娥女也得找個地方安置。」
二人理不出任何頭緒,只得相約兩日後相見。
長安城歷經劉邦與呂雉十餘年苦心經營建設,已成為通都大邑,除了人口大量增長外,更因地利之便,促使商業貿易流通率高,故不論春夏秋冬或是天晴暴雨,長安城市井無不熱鬧非凡。
不論是酒樓、飯館、茶廳還是布莊、染廠、農販、藥房、工匠、妓館、博奕賭坊等各行各業興盛至極,甚至連當舖也能大賺一筆。
故而在長安流傳一句話:「舉凡在內地賣不出去的玩意兒,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穿的,還是你家裝死人的棺木都能在這賣出去,那怕是你現拉的米田共也能賣得一錢。」
甚至在鬧市還多了新興行業─賣藝的雜耍人,這些雜耍技藝亦是多變萬化,舉凡狗皮膏藥、仙丹妙藥、踩刀山、胸口碎大石、吞火棒、武館收人、門派招門徒,稀奇古怪什麼都有得賣,至於是真是假就得憑個人運氣。
春分後第三日,長安城鬧市來了個賣藝的小娘子(漢時娘子為未出嫁女子,並非妻子。),用一種奇特的操偶術與令人摸不著頭緒的配音,表演一齣劉邦與項羽奪關中戲碼,兩隻著短袖的玉手不斷操控與交換數具人偶,講著各種不同的方言與男人雄壯豪情的語氣,令圍成一圈的觀眾如痴如醉,還未過一個橋段,圍觀的人群愈來愈多,一圈圍著一圈,初時還能維持秩序,未及一頓飯的時間,幾乎大半個市集的人都將街角堵成一團無法前進。
「這怎麼著?聚眾起事嗎?」來巡街的二位亭長從很遠的街頭就看到這副景象,後頭跟著八個下卒。
「官爺不是的,是來了個賣藝的小娘子,人氣挺旺的,要不是我這還有人要買膏藥,我立馬收攤趕去瞧了。」一旁賣狗皮膏藥的雜耍人解釋,卻讓那個買膏藥的客人不悅:「嫌我礙事嚒!」丟下膏藥走了。
「小狗子傻楞楞的說這話,那小娘子如果明兒再來,看我不給她點甜頭嚐嚐,這生意都讓她一個人賺飽,我們還要不要活!」另一攤表演吞火棒的大漢一臉忿然。
「哈哈,甜頭?我倒想讓那可愛的小娘子嚐嚐我這能令她欲仙欲死的大棒槌。」賣膏藥對面那攤的雜耍人,是一個表演胸口碎大石的巨漢,身長六呎四吋,臂膀肌肉橫生,一臉淫邪的笑容。
「是要用你手上那大棒槌還是下面那小牙籤?」手拿火棒的大漢向來與手握石槌的巨漢不和,這會又在爭那一時口舌之快,惹得周遭眾人哄堂大笑。
「去瞧瞧,怎在我們兄弟倆的地盤出了個小娘皮,若是夠水噹噹搶來玩玩。」一個較為矮小的亭長,聽到雜耍人間的對話,感到有些興趣。
「醜不拉嘰就要些保護費。」兩人露出一臉壞笑,令下卒向人群擠去。
「人家生意好是人家的本事,你們就只會逞口舌之快,所以永遠只能在街上混吃混喝。」就在這時卻有個人出聲譏諷。
眾人一聽大怒,皆聞聲望去,只見到那個人的背影欲往那擠滿人群的攤子前去,見那人身高不過六呎,理著短髮頭綁青色布帶,身著紅褐色短衣與袍褲,拿石槌的巨漢見那人還矮了自己小半截,必是可欺,竟拿著石槌向那人擊去:「滾你奶奶的!」
眾雜耍人一見不禁大呼:「小心。」「這一槌可要死人啦!」
卻見拿石槌的巨漢一槌落下就動也不動的站著,眾人過去一看。
就見綁青色頭帶的人張開粗大的手掌握住槌子的前端,嘴角微微揚起一臉不屑。
手拿石槌的巨漢卻滿臉通紅,彷如憋了一肚子的氣無處可發,眾人心道:「這可遇到真正的江湖人啦!」
未及片刻,巨漢已是滿身冷汗,且握著石槌的雙手不斷顫抖,眾人都以為這二人是在比力氣,那裡知道巨漢早已想抽回石槌,可對方不肯罷手,緊緊抓住石槌,令巨漢進退兩難暗暗叫苦。
兩人又僵持半晌,巨漢的雙腿吃不住對方的壓迫,竟然單腳下跪,而對方看來仍顯遊刃有餘。
此刻眾人才看清局勢,終是禁不住湊熱閙的氣氛大聲叫好,尤其是那拿火棒的大漢喊的最大聲。
「好啊!讓這傢伙知道人外有人,不是長得高大就可以欺負人!」大漢話未說完,就聽得像磨石子般的喀喀聲數響。
「哎唷!」巨漢猛地手上石槌一輕,後仰倒地。
「嘶─」周遭原本還有不斷叫好的聲音,剎時齊聲而停,眾人皆倒抽一口氣。
這石槌竟被綁頭帶的中年人一爪給抓成數顆大小不一的石塊,只餘下一半的石槌還連在那木棍上。
「不自量力!」這人看也不看躺在地下的巨漢,轉身便往擠滿人潮的攤子走去,留下愕然的眾人。
過往都是這巨漢碎別人胸口那塊大石,這回可是被人碎了手中的石槌,壞了吃飯傢伙,可謂得不償失。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一聲清澈悅耳的聲音彷若自小娘子手中的木偶口中唱出,這時正上演項羽落難被困,口中高唱垓下歌,身邊的虞姬也跟著應和,此時這句正藉由虞姬高歌,本該是令男人聽來會心癢癢的圓潤晶瑩的歌喉,唱起垓下歌來卻雄心壯志,隱隱約約又帶著悲慟的心情,不單單環繞於耳,更大大地震人心弦。
此句唱畢,人群中爆出驚天聲響,個個大聲鼓掌叫好,手上的銅板、碎銀紛紛往置於地上的盆子丟去。
「嘖嘖嘖,喜哥你瞧這小娘皮眉清目秀,笑起來可甜死人。」矮小的亭長輕推另一位叫鄭喜的亭長。
「還不只哩,那奶聲奶氣的聲音聽來可膩死人了,瞧那身段玲瓏有緻,我忍不住要同她享受顛鸞倒鳳之樂!」鄭喜見獵心喜。
「怎?想獨食?」
「王予,這娘皮我想讓她成為我的禁臠,十金要否?」王予聽了鄭喜的條件,想了一會才心不甘情願的同意,鄭喜心中大樂硬是將周圍的觀眾推開,擠出一條路。
「散了、散了,有人舉報這女子來歷有些問題,我們要帶回去偵查。」王予擺足了好大的架子,命下卒驅散群眾,有些觀眾發出不平之聲。
「小娘子莫怕,只要乖乖跟我走,保證沒事。」鄭喜走近賣藝的女子,雙眼登時為之一亮,心裡大讚:「怪怪個不得了,遠看已是美不勝收,近看更是水嫰嫰。」那猥褻的眼光掃向女子曼妙的身材心道:「該大的大,該細的細,該翹的翹,賺翻了!」隨即大手一伸抓住白嫰的玉手。
「咱可沒做什麼事。」女子一驚急忙甩開。
「哈,聽聽,這娘皮還說咱兒,不就是外地來的可疑人物,非好好問問不可。」鄭喜向還在驅趕人潮的下卒和王予炫耀,隨即轉身再次抓向女子:「現在咱是沒做什麼事,等會咱們就要做些快樂的事。」
女子轉身一退,讓鄭喜抓了空,她隔著裝木偶的匣箱與鄭喜對峙,他也不急,左走右繞逗弄女子。
「哈,余離長安多年,沒想今兒個大開眼見。」就在下卒還在驅趕人潮之際,遠遠傳來震耳欲聾的聲音。
「官爺辦事,還不快滾!」王予一聽環顧周遭,只聞人聲未見人影,就知道來者是個高手,有些緊張。
「想必人人都見過狗兒吠,但應該還是頭次見過狗兒會吐人話的。」不知何時,在下卒面前冒出一個服裝怪異的人。
說是怪異,其實是少見多怪,長安本是通往西域的站點,所以不時有使者自西域而來,但這時期,佛教禪學還未西進,所以對此人的服裝感到怪異。
這青年身著無袖的紅黃兩色短袍,生得高大英挺、皮膚炯黑,短髮理得極短,這人稱不上英俊帥氣,卻長得濃眉大眼有些童顏稚氣,看起來不過二十許,只是當下卒靠近一瞧,這人可不只是生得高大,恐怕有七呎高,這人一接近,整個視線都被遮住,下卒們一時驚得找不出話反駁。
「這是老子的地盤,別想來鬧事!」鄭喜這時也不再理會女子,拔出腰間的刀與那人放話。
「哈哈哈哈,有趣有趣,敢在老子面前自稱老子的人,都在地府裡找老子了!」說這話的不是站在王予等人面前的青年,而是頭綁青帶自另一端走來的中年人。
眾人回望這中年人,青年倒是友善的向中年人微笑示意。
「楞著做啥,還不快逮捕一干人犯!」鄭喜命令,王予和下卒抽出腰間的刀,分頭劈向二人。
眾人正準備打成一團,那賣藝的妙女子卻依著匣箱,手托香腮嘟著櫻桃小嘴看戲,水靈水靈的大眼眨呀眨的,臉頰還帶著淺淺的迷人酒渦,好似一切都與她無關一樣,適才驚慌的模樣全不見了。
「打呀!打呀!」原本被趕離的百姓,一見有人仗義不平,便與那些本為好事之人一同跟著叫好。
「用刀?」來自西域的青年輕笑,以掌撮刀後發先至劈了四掌,四名下卒的刀便噹噹落地,這些人並非一合之敵,四人的手痛的抬不起來。
「好身手!」中年人一邊觀察青年一邊應敵,只見他出手比起青年更為俐落,雙手並用一抓一摔,將四人絆成一團,群眾大聲叫好。
「啊!」這時,那賣藝女子看著兩人大出風頭,似乎發現什麼,驚呼一聲。
「咳!二位英雄別亂來,這只是一場誤會!」王予見狀,趕緊將刀送回鞘,兩隻手高舉著閃到一旁,留下鄭喜一人面對。
「別、別過來!」鄭喜邊退邊叫囂。
「有見過搶人欺女之事,但像你這等不長臉到在光天化日之下強搶女子的人,倒還是頭一次看到!」青年爽朗的笑了笑,並未再向前走,鄭喜看向中年人,只見那中年人也停下腳步。
「你來自西域?」中年人輕蔑的眼神看了鄭喜一眼,隨即轉向另一頭。
「正是。」
「請賜教!」中年人不理會青年是否應戰,一雙鐵臂向青年橫掃而去。「來的好!」青年似有準備,仍以右手為刀改劈為拍,一掌拍向鐵臂,藉力向上翻了一圈,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下劈往中年人。
一招失步步失,這是武技人為了顏面而不懂進退之理,真正的高手不會讓自己陷於這樣的狀況,中年人亦是如此,他抬頭望向青年,青年背光他卻向陽,一時之際看不清青年的攻勢,瞇著雙眼迅即大退三步,避開這招。
青年這招劈了個空,落地雙腳一蹬,突擊刺向中年人。
「好!」中年人大叫一聲,並非只是胡亂大吼,而是用丹田發氣,一面聚氣制敵,一面用吼聲擾敵,中年人站在原地動也不動,欲使一招碎天滅地硬接對方的突擊。
只見青年的右手以割風破刃之威刺向對方胸前一寸,中年人則是化拳為掌接下這招,緊緊夾住對方右手,令對方分寸未進。
兩人出招拆招不過須臾,好事的觀眾卻是首次見到如此精彩的比鬥。
在眾人面前,中年人像使了個空手接白刃,只是這刃非真刃,卻是化掌為刀的肉掌,而中年人這招碎天滅地本是雙拳力壓,現在卻以掌代拳使出。
青年與中年人兩人皆心知肚明,對方本是試探皆未使出本事,兩人相視而笑。
「小心!」伴隨賣藝女子的警告,四支袖箭竟無聲無息向兩人激射而去。
「嘿,二位老弟,這等好玩之事怎可不讓我參一腳?」聲未至,人已到,只見這身影踏空而來,二腳有如踩階梯,硬是將二支袖箭踩下去,卻見那袖箭居然一分為四,二分為八,化為八支黑漆漆的小箭,被踩落地的竟只是個空殼。
「踏雲梯!」「丰老!」兩人見到這人身手非凡,不約而同開口,只見那西域青年大喊踏雲梯,綁頭巾的人卻叫著丰老。
「子母箭,小心有毒!」來者正是施展踏雲梯的丰老,只是丰老舊力已盡新力未轉,未能及時踩下子母箭而警告兩人。
這被西域青年所認出的踏雲梯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招式,其實只是一個蹴鞠的花招,西漢時代娛樂活動並不多,但蹴鞠可說是全民運動,舉凡窮人、富人、大人、小孩或老翁都會玩的遊戲,甚至女人也能玩。
簡單來說,蹴鞠是一個踢球的遊戲,但在秦朝前它是一個軍隊的訓練項目,秦後漸漸演變成一個娛樂活動。漢代後,軍中仍保留此項目,但在劉邦大力推廣於民間後,蹴鞠成為非常專業的運動,且還有明定的比賽規則。
踏雲梯則是劉邦在宮中建立蹴鞠場時,所發明的一個球技,以腳踩地而凌空,再踏鞠球躍於空中,另一腳同時將被踩下的鞠球勾起來,週而復始。
爾後劉邦將其發展為個人的獨特輕功,要能在空中不斷換氣與提氣才能保持在空中而不墮,如在空中可以躍高,若履平地可借力使力速度更快。
而踏雲梯的動作,不只包含踏、踩、瞪、踢,故亦有人稱作上雲梯、上雲踢、踏雲踢,然而自劉邦創立以來,幾近無人可運用此獨特輕功,而丰老卻是極少數會此輕功的人。
兩人聽從丰老的警告不及細想,中年人拔腿向那袖箭奔去,西域青年卻是後發先至,右掌輕輕自下往上撩撥,竟是將射向他的母袖箭整個翻轉過來後脫殼,分為四支子箭脛自射向那四支毒箭,無一漏去,叮叮噹噹八支毒箭分別掉落。
另一邊,中年人奔向毒箭大喝一聲,表情猶如怒目金剛,胸腹肌肉緊收,竟是不理會那支未分離的母袖箭令它射入懷中,接著大手一抓硬是將射向自己的四支子箭抓在手中,中年人瞧著手中四支黑漆漆的毒箭一眼,隨即棄置於地,再將懷中未分離的母袖箭取出兩手一折,將裡面的四支子箭一併折斷。
兩人不約而同望著丰老,此時丰老早已解決暗地偷襲的鄭喜與王予,二人躺在地下動也不動。
「把這事一五一十和你們官老爺交代清楚,就說是我丰老幹的,若有任何隱瞞,他們就是你們的下場。」丰老指著鄭、王二人,令下卒們將屍首帶回去覆命。
「原來這功夫叫踏雲梯。」中年人向丰老讚嘆。
「哈哈,我正準備去醉仙樓等王老弟,沒想到在這遇著了。」
「我也就是在這閒逛,待得午時就往醉仙樓前去赴約,至於這位俊才……」原來此中年人正是與丰老約好春祭三日後見面的老王,老王正欲介紹西域青年,卻不知如何稱呼。
丰老見著這青年,卻咦了一聲。
「老哥哥,多年不見,這踏雲梯似乎落下啦,怎沒幫小老弟全擋下來。」西域青年露出與炯黑皮膚完全相異的一口白牙,口中雖然聽似埋怨,卻可從對話中看出他與丰老相識多年。
「這不是項老弟嚒,你可讓老哥哥盼望許久,你若再不回來,我就準備去西域尋了。」一老一少,二人熱情的抱成一團。
「這江湖路還真是小。」一旁的老王見狀心道。
「閒話莫提,走,先去醉仙樓。」丰老雖見故友,但也未忘新友,一手一個領往醉仙樓,丰老離開前對著賣藝女子點頭示意後便離開,留下這賣藝的俏美人暗自跺腳。
自古以來,文人騷士以文會友,而江湖人自然是以酒會友。
江湖人常言:不會喝酒非好漢,能喝二十斤酒方為英雄。
西漢時代制酒技術並不算精緻,因而酒水品質優劣不一,所謂酒水自然就是因為酒精濃度低,嚐起來淡如水,故而稱酒水,所以喝個二十斤並不算多,大多為慘了水的酒。
丰老拉了兩人前往醉仙樓三樓廂房,跑堂的急忙端了十大罈白乾上來,弄了整桌的烤羊全餐,還點了鮮魚筍湯、四色糕點、三道甜品。
丰老先向來自西域的項姓青年介紹邪王卜邪:「該叫你老邪還是卜老弟?」
「承蒙丰老看重,喚我卜老弟即可,江湖人隨便慣了,可別學那些文人叫那虛偽又肉麻的賢弟就好。」卜邪哈哈一笑。
「至於這位……」丰老向卜邪介紹眼前的人,原來這位來自西域的青年叫項刀,約莫五、六前自長安去往西域,實際上項刀也不算年輕,今年也有三十,只是憑著那有些稚氣的臉龐與爽朗的笑容,看起來約莫二十餘歲。
丰老對項刀簡略說明這幾年他遠赴西域後,漢朝所發生的一些大事。
「我離中原已久,西域貿易發達,消息卻不通,殊不知這些年的變化,且不論朝廷變化如何,余誠心佩服,卜兄好霸氣,雖然江湖不比朝廷,但雄才大略更勝諸呂,方可為巴蜀一霸。」
「不敢,一切皆因緣際會罷了!」卜邪無奈苦笑,落寞的神情一閃而逝,卻未逃過丰、項二人的注意,兩人亦知與卜邪初識,言語間不宜深談,也就很識相的沒有多問。
三人吃吃喝喝談天說地,這頓酒飯吃了足有二個時辰多,滿桌豐盛的菜餚只餘空盤,十大罈酒也喝到見底,之後又讓人上了幾壺濃茶解解酒膩。
三人聊天內容,多是丰老與項刀講這幾年做了那些事,少部份才是項刀談些西域風情,卜邪雖然少言不太談及與自己有關的事,但也提了許多有關巴蜀一帶的風俗人文趣事,氣氛頗為熱絡,早已沒了先前拘束的感覺,三人相談甚歡。
項刀素來佩服一方霸主,再加以今日與卜邪一談,更覺得卜邪有一種與父親神似的氣度。
「老哥哥、卜兄,小弟有一事相求。」項刀一臉正經。
「但說無妨。」丰老饒有興緻看著項刀。
「無須避諱。」卜邪點頭。
「席上小弟最為年幼,早年與老哥哥結識,以父兄敬之,今日雖與卜兄初識,卻十分敬佩為人氣格,頗有相見恨晚之情,因此想高攀兩位兄長結為義兄弟。」
兩人聽畢態度迥然不同。
「混小子,與卜老弟是相見恨晚欲為義兄才是真,同我可是相見恨早。」丰老佯怒譏笑,項刀臉皮倒也挺厚的,只是嘻嘻一笑。
卜邪卻沉默不語,待得丰、項二人眼神皆注目,卜邪才道:「承項兄弟看得起,只是邪王聲名狼籍,惡名怕是累了二位。」。
「哈哈,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這天下人對於畏懼、無知之事皆以此理判斷,卜老弟若真是惡名遠播,又何必擔心累名於我等兩人?」
「正是,我等結義不求其利,只為景仰卜兄為人,故而厚顏薄恥一問,項小子今日若因他人閒言閒語而錯此機緣,小子又與那些市儈之人只為謀利而行便己之事又有何差別。」
卜邪看著一臉真誠的項刀,又望向丰老,只見他微微點頭。
「既然如此,如果老─我再拒絕就是不識抬舉!」卜邪難得露出一抹笑容。
「這句話可折煞小弟!」
「好!今日居然可與二位英雄俠客、一方霸主結為兄弟,這是老兒我風燭殘年之際最樂事,只是得委屈你們。」
「委屈?」兩人不解丰老的意思。
「人說與兄弟結義交換金蘭譜,便要立誓約同生共死,老兒我行將就木……這不委屈你們了,哈哈!」
卜、項二人大笑。
「江湖人便宜行事無須麻煩,今日以茶代酒。」丰老推開廂房窗子,天上烈陽已落,已是戌時之後,跪在窗下,項刀與卜邪分別跪其兩邊,丰老將茶壺取來,自懷中拿出細針在指頭上刺血滴入壺內,卜、項兩人照著做,最後項刀自壺內倒出三杯茶,三人雙手持杯高舉頭頂向天一拜。
「皇天在上,我丰老有幸與二弟卜邪、么弟項刀結為異姓兄弟,今後我等三兄弟異姓同心,富貴貧賤不相棄,兄弟情誼不背離,雖未同生,但求共死,以此心明鑑!」三人宣誓完畢,飲盡杯中物,終成異姓兄弟。
「哼哼!」三人起身後,丰老卻一臉不悅看向項刀。
「大哥怎了?」卜邪疑問。
「我說項小子不誠心。」
「怎這麼說?老哥哥。」項刀彷彿心虛般聳肩道。
「適才說到但求共死這句,我怎聽到你的聲音猛然小聲許多。」丰老向項刀責問,卜邪一聽哈哈大笑。
「沒這回事,小弟我說的最大聲,我願與丰老共死同穴。」項刀嘻皮笑臉,卜邪倒了杯茶給項刀,讓項刀向丰老賠罪。
丰老將茶領來飲了,又叫跑堂的送了二罈酒,點了幾樣口味較淡的菜色,三人又是吃喝一陣,丰老卻是醉了,最後在醉仙樓要了三間房住下來。
「認識老哥哥那麼多年,頭次見著他醉成這樣。」項刀和卜邪將丰老送回房間,兩人就在卜邪的房間點了壺清茶聊開了。
「雖與大哥不過相識二日,但我覺得大哥比起一般江湖人更有一種深沉的氣魄與的穩重的濬智,很能吸引眾人與他結交。」
「小弟亦有同感,對了,適才聽二哥說來長安是想來辦些事,不知是否有需─」
忽地,一陣乒哩乓啷聲響打斷項刀的話,茶壺水杯摔落地上的聲音自隔壁丰老的房間傳來。
「老哥哥醉暈了,連茶杯都握不住。」項刀起身準備去看看。
「啊─」一聲蒼涼沙啞的嘶吼響徹醉仙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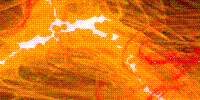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